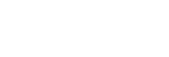无论是商场里的价格牌,还是网上调侃时常说的“车厘子自由”,用到的都是这个
将外文专有名词音译成中文一直是许多译者头疼的问题,读者们也常常被各种译名搞到头昏。
比方说,你可能很难将粤语译名“祖高域”和著名网球运动员德约科维奇(Djokovic)联系在一起,不过如果你用粤语读一遍,大概就能理解了。
除了从粤语中流传来的外来词,许多早期使用过的音译名词,今天看来也非常奇异。
《英汉互译实用教程第四版》中解释道,上世纪我国在专有名词翻译中缺乏统一规定,因此就催生了很多不同的译名,再加上无法重新出版过去的书籍并订正译名,多种版本的译名也就流传开来。
类似的,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早期叫做“嚣俄”,可能是因为[hju]的发音与粤语中的“嚣”字很像。
另外莎士比亚(Shakespeare)被译为“狭斯丕尔”。《天演论》里,严复把伽利略(Galileo)译为“加理列倭”。
另外一本在清末为了“富强救国”而出版的书也是充满了早期的专有名词翻译,该书是郑观应编纂的论文集。其中就有很多地方的译名。
比方说,他把牛津(Oxford)翻译成“敖斯佛”,剑桥(Cambridge)翻译成“堪比立”,在现在看来最有趣的是把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翻译成“哈吧书院”,另外还有哥斯达黎加(Costa Rica)翻译成“考斯他立楷”。
除了人名和地名之外,有一类抽象名词,从前并不存在于汉语中,是许多前辈译者翻译到中文里来的。比方说逻辑学(logic)从前被严复翻译成“名学”,孙中山甚至把它翻译成“理则学”。
Abstraction(抽象)被他翻译成“玄摛(chī)”,他还把philosophy(哲学)翻译成“致知”。
跟马相伯运用中文概念的方式不同,严复可能是个音译狂魔,他把liberty(自由)翻译成“里勃尔特”,另一个“自由”,freedom,翻译成了“伏利当”。
严复的音译还包括英里(mile)“迷卢”,神经(nerve)“涅伏”,和斑马(zebra)“芝不拉”。
看到这,你应该对而今我们熟悉的译名在此前有多少千奇百怪的译名变体有了大概了解。不过,译者们是怎么解决这种混乱的呢?
中文音译里的“英格兰”“巴黎”“柏林”,以及“罗马”都是遵循了这一原则。
汉字都是单音节的,只有一个音。要解决音译中的混乱问题,就要固定一些汉字来对应外来专有名词中的特定音节。
比方说萧伯纳、雅典、牛津、剑桥等等这类名字要么是汉字音不准确要么就是翻译上很怪诞。
我们不会改变这些音译名亦或重译。要是这么做了,反倒可能给读者造成新的混乱。
但是不管这些专有名词在现在看来多么搞笑和奇怪,它们都是百年前的译者们打开窗,捧在手里传递下来的第一束光。
本文由:欧博abg登录入口网页版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