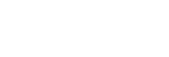“除了斐济语课,其他都是英文授课,孩子们平时也都讲英语。” 班主任Paul回答我说道。
那岂不是比我英语还好,我能教得好他们么?我心里想着,对自己产生了怀疑。那时的我刚开始留学生涯,英语还很蹩脚。但一次和陌生人偶然拼桌的对话,促使我来到斐济苏瓦的这所小学,成为教学项目的志愿者,并为毕业后的我选择当老师埋下了一颗种子。
接受了22年国内教育的我,在考研失利后迅速决定出国留学。选择留学国家时,脑海中第一个蹦出来的就是澳大利亚。回想起来,这个选择有些奇妙。源于我之前看过的一档央视综艺,节目中有一个女孩在PK中国文化知识中胜出,发表感言时说自己即将要去澳大利亚墨尔本读书,我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我也想去墨尔本读书。那一刻我自己都有些惊讶,因为在那之前我未去过澳大利亚,对澳洲的印象仅限于悉尼歌剧院和袋鼠。但那一刻,我与墨尔本的链接悄然产生了。
我本科读的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新能源方向,学了四年的专业,拿到过专业第一,也获得过国家奖学金,但说实话,我谈不上喜欢。当时的我不清楚自己到底喜欢什么,也没思考过将来想做什么。出国选留学专业时,也只是顺理成章地继续了我本科的专业,选了电气工程。听中介说这是移民专业,当时的我对移民没有概念,只觉得多一个选择没有坏处。
到墨尔本的第一年,我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学校,重心放在专业课的学习上。虽然本科在国内学过相关课程,但用英文学习起来一点也不轻松,每天需要花大量时间预习和复习课程资料,挂一门课要4500澳元(两万多人民币)重修,我可挂不起。于是,和在国内上大学时一样,我还是天天泡在图书馆,没有精力参加活动社交。
最头疼的还是用英文和外国同学交流。刚开始连加减乘除法的英文都说不利索,只能边听边模仿,勉强可以交流学术问题,但也仅限与专业内容。墨尔本的中国人很多,我大多数时间和中国同学、中国室友呆在一起,没有主动和外国人交朋友,因此我的生活英语十分匮乏。
七月,南半球的寒假,短短三周半的时间,我不准备回国,但也没想好要做什么。一天中午,我独自来到学校对面的中餐馆。那天餐馆生意很好,三个中国学生过来和我拼桌。等餐时,我们聊了起来,原来大家是校友。聊到放假计划时,其中一个姑娘说她是国内一个义工组织的成员,并向我介绍了他们的国际义工旅行项目。这种一边旅行一边做志愿者活动的方式吸引了我,我立即询问如何报名参加。那位姑娘和我互加了微信,并把报名网址发给了我。
回到公寓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网址链接,网页上有很多旅行目的地可供选择,斐济,这个和澳大利亚同在大洋洲的国家,第一个映入我的眼帘,其他还有巴厘岛、马来西亚、斯里兰卡、肯尼亚等国家。由于这次是第一次见面的人提供的信息,我本能地保持了警惕,在网上认真确认该义工组织的规范性,了解到他们与全球最大的国际义工及志愿服务项目运营方合作,倡导“负责任、有意义”的旅行,在确保安全可靠后,我递交了申请。
这次选择虽然又是跟随第一直觉,但我在异国的独自生活中多了一份慎重。首先,我考虑了签证问题,仔细浏览网页介绍确认了斐济对中国护照持有者免签(刚好在2015年开始实行),这样我不需要预留时间办理签证。其次是距离、时间和机票问题。墨尔本有直飞斐济楠迪机场的航班,飞行时间只要四个多小时,项目日期有合适的航班,价格也在预算范围内,完美匹配我的预期。
锁定目的地后,我当天递交了报名申请,国际项目对申请者的语言有一定要求,雅思成绩帮我免去了面试环节,一周内就通过了申请。我选择了普通的六人间住宿,支付了4500元人民币后,一切准备就绪,等待开启斐济两周的义工旅行。
申请通过的一周后,我坐上了前往斐济的航班。一下飞机,湿热的气息扑面而来,穿长袖的我没走几步就出了汗。机场墙上的宣传画中,一张张皮肤黝黑牙齿洁白的笑脸,让我提前感受到了斐济人民的热情好客。楠迪机场比我想象中的老旧,面积不大,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出口,零零散散站着几个人,我开始寻找来接我的人。
一个看起来像当地人、身体壮硕、比我年长的姑娘双手举着印有绿色The GreenLion手写字样的白底牌子,我朝她走过去,准备进一步确认,还没等我开口,她用英文问到:“你是Angel吗?”我点了点头,回答是的。她简单介绍了自己是协调员Eta,让我和她再等一下和我同班飞机的另外一个志愿者Effy。不一会儿我们等到了,Eta去买前往苏瓦的公交车票,我和Effy在公交站牌处等待,便聊了起来。
Effy是澳洲人,只有19岁,她前一年开始间隔年,去了50多个国家旅行。之前我只在杂志上偶然看到过“gap year”这个词汇,Effy是我接触到的第一个讲自己间隔年的真实的人,两个英文单词好像突然从纸张上蹦了出来,在那一刻具像化了,也让我意识到原来一年可以去这么多地方,可以做这么多事情。
Eta买好了票回来,招呼我俩上车。一辆车窗只有框架没有玻璃的老式公交车开了过来,仿佛一下穿越回了国内的七八十年代,刚上车时的我还处于兴奋之中,心想这四面通风的车窗挺特别,可以自由呼吸新鲜空气。
车上空座不多,我们三个挨着坐在了最后一排,从楠迪机场开到首都苏瓦要将近四个小时,出机场没多久,行驶上了土路,公交开始剧烈颠簸,晕车的我感到一阵恶心,只能自我催眠,赶紧睡着就不会吐了。
吹了一路的风,醒来时,眩晕伴随着头疼,贴着座位部分的衣服早已经被汗水浸湿,头发凌乱得像梅超风,身体的不适感占了上风,我已无暇去顾及形象。还没等我舒一口气,又被告知还要坐出租车才能抵达营地,营地在距离苏瓦市中心半个多小时的郊区,和四个小时相比,半个小时显得没那么难熬了。
到营地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天已黑透,没有亮着的路灯,借着皎洁的月光,推开营地的大门,一个有着扁三角形屋顶、方方大大、黑乎乎的“集装箱”出现在眼前,这就是接下来要住的地方。
进入室内,Eta熟练地开了灯,放低声音说大多志愿者已经入睡了,告诉了我和Effy各自宿舍的具置。营地总共两层,地上一层和地下一层,Effy住在地上一层,我住地下一层,要从外面下楼梯过去。
我像寻宝一样,独自摸索。宿舍已经熄灯,打开手机自带手电筒,寻找贴有我名字标签的床,六人间放三张木板床、上下铺,没有多余的家具。我住下铺,抬头看了眼上铺的名字,Ke,心想应该是中国人。床已铺好,蓝白条纹的床单和枕套,残留阳光晒过的味道。
我赶紧去了淋浴间,里面只能容纳一人,但却凌乱地摆放着好几瓶不同牌子的洗发水、沐浴露,猜测应该是大家存放在这里的,人多的时候估计还要排队。打开龙头,发现只有冷水,没人可以问,无奈冲了个凉水澡。后来了解到营地用的是太阳能热水器,在固定的时间段内才提供热水。
终于躺床上了,习惯性地打开手机看消息,才意识之前忘记买本地电话卡,也忘了开国际漫游,手机完全没有信号。这时,上铺的姑娘回来了,她就是Ke,主动用英文和我打招呼,听到她流利的英文,我没好意思问她是否是中国人,只是用英文简单问了营地的Wifi,然而手机没信号,英文不自信的我没有继续和她多聊,心想算了,先睡一觉,醒了再说。
第一晚和Ke的对话,让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母语安全感被打破的感觉。在墨尔本,至少有中国同学和室友可以依赖,而现在只有我一个人。
第二天早上,闹钟还没响,我就爬了起来,发现同寝室只剩下一个女孩,其他室友都已出门。女孩叫Tola 她主动对我说“Morning”,并告诉我可以去一层吃早餐,她准备先过去。当看到她明媚的笑脸和温柔的深褐色双眸,我内心笼罩的阴霾开始慢慢消散。
洗漱过后,我独自前往一层吃早餐,看到大家的鞋子都放在外面,我也学着脱掉鞋子,光脚进屋。营地提供西式自助早餐,有煎蛋,炒蛋,面包,生菜... 还挺丰盛,手机到地面有了信号,我抓紧给家人朋友发微信报平安。我们住的地下一层路由器不好穿透,以后回宿舍就得回归原始生活了,享受没有手机打扰的清净,好像也不错。
早餐过后,还有一小时才集合。大家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我站在原地四处张望着。这时,Tola向我招手,邀请我加入他们的聊天。她窈窕高挑,有着健康的小麦肤色和黑色长卷发,在人群中十分夺目,被女神邀请,我按捺住内心的兴奋,加入了其他志愿者的对话,还一起玩了一轮扑克牌,和外国人互动比想象中轻松有趣。我的不安全感逐渐被好奇感替代。
协调员Eta召集大家集合,客厅铺着好多条色彩鲜艳的毯子,大家围成圆圈坐在一起。我大致数了下人头,有30多名志愿者。第一个环节自我介绍,Eta点名说从我开始,我竟然有一种中大奖的快乐,欣然接受并即兴完成了。我发现自己实际比想象中的要勇敢,想象中的那个我大概率会紧张和局促不安,然而身处当时的环境,我的兴奋大于畏惧。
那天起,我不再恐惧无法用母语交流,一切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就像学骑自行车一样,当原本可以依赖的第三个轮被拆掉时,本能地就学会了只用两个轮来平衡。
大家相互认识后,Eta讲解了两周的行程安排。第一周所有志愿者一起,在营地学习简单的斐济语,体验当地的烹饪和编织,同时也会组织大家去苏瓦市区参观游玩,第二周开始会分组进行志愿者项目。
根据大家的自主选择,志愿者们被分到了不同的组,我所在的是教学组,此外还有体育,建设,幼儿园及海龟保护组。教学组和体育组的志愿者会被分配到不同的小学,协助学校的老师分别进行学科和体育教学,同时帮助学生了解外界的新鲜事物和文化;建设组的可以参与筑地基及上灰泥等工作;幼儿园组的则是到幼儿园照顾年龄较小的孩童,提供情感支持并进行辅助教学;海龟保护的需要去海边进行海滩清理等环境保护工作。所有的项目都不需要志愿者有相关的专业背景和经验,只需要参与者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可以创造和改变。
项目介绍完毕,营地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卡瓦敬酒仪式,据说这是斐济人对贵宾的最高礼遇。Kava盆(看着像一口黑色的铁锅)放在志愿者们包围的圆圈中央,营地的几位工作人员坐在Kava盆旁边,她们先是往盆内加入之前准备好的矿泉水,然后将胡椒树根的粉末在盆内揉搓成浆,制成Kava(卡瓦),用木碗乘出,大家传递着轮流饮用。
仪式完毕,Eta向我们强调了斐济当地的一些习俗和禁忌,比如进门前要先脱鞋,这是当地的习俗;不可以去摸小朋友的头,会被认为是对其家人的不尊重,尤其提醒之后需要到学校接触当地小朋友的志愿者们多加注意。
午餐是当地的美食,营地准备了纯素食,印象中有木薯,食物大多淋有柠檬汁、辣椒粉和胡椒粉,吃下去,口腔中弥漫着酸酸辣辣的味道,像是直接吞了柠檬和辣椒似的,调味料盖过了食物本身的味道,刚开始尝试还不太习惯,但是一场新鲜的味觉体验。
吃过饭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最近的超市采购,步行过去只要10分钟左右。终于欣赏到了营地外的风景,门外是一条只能过一辆车子的土路,路两边栽满了绿油油的椰子树,上面挂着还未成熟的椰子,周围都是大集装箱似的村民住宅,单层居多。习惯了被城市的高楼大厦包围,眼前的风景让我感觉到平静。
在超市买到了久仰大名的斐济瓶装矿泉水FIJI water,据说奥巴马都爱喝,当地只要2斐济币(约6.5人民币),还是非常实惠的。另外还入了必备的驱蚊水,斐济的蚊虫很多,一晚上被咬了好几个包,由于前天晚上睡得太香,早晨起床才发现。
斐济属热带海洋性气候,年均气温在20-30摄氏度之间,冷热适中,整体来说比较舒适。5-10月盛行东南信风,是相对干燥的季节,但7月的斐济依然阵雨频繁。返回营地的途中突然下起一阵,空气中夹杂着湿润泥土的气息,我们在雨中奔跑,体验踩小水坑的欢乐,感受着久违的大自然疗愈。
自我介绍环节中,我发现营地原来是有中国小伙伴的,其中一位中国阿姨主动来和我打招呼,她叫Linda,在国内一所高校当英语老师很多年了。阿姨用中文对我说,她的女儿也在墨尔本念书,比我小几岁,假期她们一起来到斐济义工旅行,母女俩搭档做志愿者。阿姨和我恰好还都在教学组,分外投缘。
隔天下午,协调员组织我们到苏瓦市区参观。那天因为女儿身体不太舒服,Linda阿姨只能自己一个人跟着大堆参观。阿姨虽然在国内大学教英语,但对于和外国人讲英文还没有足够的信心,我这个刚打破母语舒适区的人临时给她当起了翻译。
在苏瓦市区,我终于可以买当地的电话卡了,刚好Linda也要买,我帮她用英文和店员沟通。第二周教学项目就要开始了,到时我和Linda会被分到不同的班级,她也需要独自去面对斐济的学生们,我不可能一直陪在她身边。于是我开始鼓励Linda尝试自己用英文去表达,实在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我再开口帮助她。
我们逛到一家甜品店,Linda想给女儿打包一份当地的甜品,这回她试着直接和店员沟通,不确定时会看向我,我在一旁点头,示意她没问题。Linda成功买到甜品,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仿佛看到了一天前的自己,对自己的英语水平也多了些信心。
苏瓦市区临海,街道两旁栽满了绿树和鲜花,在这座花园城市中游走,悠闲惬意。夜色渐浓,返回营地的我们再次坐上了斐济公交,市区的公交比机场坐的那辆要时尚一些,车内被装饰得花花绿绿,还放着欢快的音乐,车子开动起来,感觉自己置身于一个移动的卡拉OK厅。公交依旧没有窗户,阵雨突袭,窗外的塑料帘子被放了下来,不用担心被淋到。雨水从透明的塑料帘子不断滑下,隔着塑料帘子看向窗外,市区夜晚五颜六色的灯光变得愈加梦幻。
晚上回到营地,我主动和住在上铺的Ke用英文聊了起来。去市区游玩的跳水活动中,她是为数不多敢于跳下去的几个人之一,我被她的勇气感染。自我介绍环节我确认了Ke是中国人,在加拿大读高中。那晚Ke和我聊到,她平时会和当地的朋友玩,生活方式已经非常西方化了,所以即使和中国朋友交流也会习惯性地用英文。我羡慕着Ke流利的英文,同时开始担忧即将开始的教学项目,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胜任。
第二周,教学项目正式开启,我被安排到了苏瓦当地的一所政府小学,学校由政府提供免费的基础教育。学校上午8-12点安排学术课程,如英语、数学课,下午1-3点则安排辅助学科和活动,如手工、体育课,因此营地教学组(我所在的组)的志愿者每天早上要集合去学校,辅助学校老师上午的教学,中午开始可以自由活动;体育组的志愿者下午再过去学校进行交接。
第一次访校,协调员带领我们一起乘公交抵达,印象中车程在一小时之内,离营地不算太远。这所小学整体占地只有国内学校操场的大小,在公交站牌处俯瞰,学校全貌可以尽收眼底。
学校的第一站是校长办公室,这里也是学校其他老师的办公地点。校长见到我们时,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Bula!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学校!”他的声音洪亮而温暖,仿佛带着南太平洋的阳光,再次让我们感受到了斐济人特有的热情好客与真诚。他根据协调员整理的志愿者基本信息,为我们依次分配班级,以协助当地老师的教学工作。
“你在墨尔本大学读工程硕士呀,那来高一点的年级,六年级(斐济的政府小学八年制)当助教吧。Mr. Paul是603班的老师,你们认识一下。”校长难掩喜悦地说道,随后叫了在里屋办公的Paul出来向我介绍。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Paul,一位身材高大、皮肤黝黑的中年男子,乌黑浓密的头发略带自来卷,戴着褐色细边框眼镜,上身短袖花衬衣,下身裹着蓝灰色的sulu(苏禄裙,斐济男女都可以穿),脚上是一双简洁的凉鞋,经典的斐济式穿搭。
Paul热情地对我说:“Bula”(斐济语“你好”)并和我握手。我回以“Bula”,然后开始和Paul用英文沟通。
“我一个人负责教所有的科目,英语、数学、斐济语、健康课、自然课......”
在来斐济之前,我只知道当地的大部分居民无法负担旅行的费用,村民们很少有机会与外界接触,学生们也难以了解外界的新鲜事物和文化。但我没想到,一所政府小学的师资竟会如此匮乏,一个老师要教这么多科目。若是换作我,一定会分身乏术。我开始对Paul心生敬佩,同时也希望尽自己所能协助他的教学工作。
Paul带我走进了603班的教室,三十个学生一齐望向我,看到他们清澈的目光,微笑的脸庞,我进班时耸着的肩膀自然放松了下来,开始用英自我介绍。当说到自己我从中国来时,班里唯一戴眼镜的男生面露激动,被我捕捉到了,于是我问道:“有人知道中国吗?”
“我知道中国,我的父母常年在中国工作。”戴眼镜的男生回答道,然后他突然用中文对我说“你好”,我本能地用中文回应“你好”。
异国他乡,一个斐济男孩会讲我的母语,我包裹着的壳渐渐裂开,任由外面温暖的空气流淌进来。
“可以教我们中文吗?”有学生问道,“我想学中文!”“我也想学!”教室一下子热闹了起来,“你好”的对话竟然意外激起了孩子们学习中文的兴趣。我看向Paul,征求他的同意,Paul爽快地点头答应,并说随后的几天内会为我预留一节课的时间上中文,孩子们高兴地欢呼起来。
中文课教什么呢?在来之前我可完全没有想过要给斐济孩子们上中文课,这个问题开始在我的脑海中萦绕。直到有一天我听到他们用斐济语唱歌,虽然听不懂在唱什么,但孩子们天籁般的歌声深深打动了我,于是我决定教他们唱中文歌。
上课前我已经用粉笔把小星星的中文歌词抄写在黑板上了。“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我把第一句歌词朗读了一遍,让学生们对汉语拼音有个初步的印象,然后以a为例帮助他们熟悉拼音的四声调,用嘴巴读“啊”的同时,我的脑袋、右手也一齐跟着声调的方向夸张地移动着,学生们模仿着我,一个个读的同时也移动着小脑袋,有的身体也跟着摇摆了起来。如果此刻关掉声音,窗外的人可能以为我们在上舞蹈课。学生们不一会儿就学会了拼音四声调,果然肢体语言全球通用。拼音一时半会儿也讲不明白,我便自创了半英文字母半拼音的“四不像”标注法,带着他们读出了歌词中的每一个汉字,再搭配上旋律,他们既学会读也学会唱了。
一节课孩子们学会了完整版的小星星和生日快乐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合唱结束,我为他们鼓掌,也为自己鼓掌。
我每日在班上旁听,Paul放心地将学生们各科目的作业交由我批改,我仔细地检查并用红笔批注,发放给学生时,我会一一告诉他们出错的地方,提醒他们订正。学生们渐渐和我熟了起来,一到课间就会围过来找我聊天。
因为想要和学生有更多相处的时间,下午我选择继续留在了学校,在远处看体育组的志愿者们给他们上课,学生们换上了自己的运动服,在操场上肆意奔跑,一个个活力满满,能够看出来学校平时还是很注重学生的体育锻炼的。
教学一周过半,我们教学组的几个小伙伴一起外出给学生们挑选告别礼物。斐济人均GDP(约5600美元)虽然在南太平洋岛国处于中上水平,但相对其他国家来说并不算高,属于中等收入国家,而且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我们所处的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这些天的相处,我发现603班很多学生的橡皮快用秃了还舍不得换,一把尺子传来传去一起使用,班里只有少数几个孩子拥有在斐济价格相对昂贵的彩笔,我们商量决定送学生们文具。
周五是教学的最后一天,当我走进603班,Paul双手捧着鲜花花环向我走来,并亲自为我戴上,说学生们为我准备了欢送仪式,斐济真的是一个注重仪式感的国家,心想还好我当天有早起简单收拾了下自己。我顺着Paul的视线看向讲桌,上面摆着一个洒满巧克力粉的圆形蛋糕,旁边还放着分蛋糕用的、绑着粉色丝带的小铲子,是精心布置过的。Paul引我坐在讲桌后的凳子上,让我对着蛋糕许愿,这时孩子们齐声唱起了生日快乐歌,正是中文课上我教他们的那首。恰好再过几天便是我的生日,这意外的惊喜同时成为了我难忘的生日礼物。
歌声响起的时候,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感觉到鼻子酸酸的,像在做梦一样。歌曲结束,我依然在梦里沉浸,不记得是谁何时把蛋糕递给了我,我惯性地吃了起来,这个梦有了味道,甜丝丝的。
学生们为我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信的具体内容已经模糊,但Pual为我朗读的画面依然清晰。一遍读完,Paul自言自语道:“Angel可能没有完全听懂我讲的英语,我再来一遍。” (Paul的英文略带当地口音,之前他说话快时,我有表达过没听清楚,他还记得。)被感动到想哭的我突然被他逗笑了,学生们也在下面大笑起来,我们一起听着Paul第二遍声情并茂的朗读。
我语无伦次地表达了对大家的感谢,当时自己说了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我始终沉浸在那个充满泡泡的、绚烂的梦里,不想醒来。
课间,学生们纷纷来找我,送我他们各自准备的礼物。有亲手用橡皮筋编织的笔套,有收藏的零食袋里送的戒指,有自己喜爱许久的贴画...还有一个手工编织的篮子,是班上一个小姑娘的奶奶亲手编的,那天她请假没来,让Paul转送给我的。我在营地学过当地的编织,单是编织一个小小的手环就要一两个小时,编织这么一个篮子需要花费多少的心血啊,这是一份厚重的礼物。遗憾的是,我没能见到那个小姑娘和她的奶奶,亲自表达我的感谢。
赠送完礼物,Pual召集班上所有学生到操场上和我拍大合照。照片上他还是身着那套第一天初见时的衣服。斐济孩子们有很强的镜头感,每次拍照,都可以捕捉到他们夸张而充满生命力的状态;面对镜头时,他们丝毫没有害羞和拘谨,面部表情和手势总能迅速到位;他们的热情似乎是与生俱来的,总是主动向我靠近,帮助慢热的我打开了自己。
戴眼镜的男生给我们拍的照片,他本人没能出现在合影中,但他的模样深深刻在了我的脑海中,成熟且睿智的他组织了全班同学签字,还写了封Thanks song送给我。
回到墨尔本不久,新学期开始了。我变得更加勇于表达自己,也能够与国外同学讨论学术以外的话题,成为生活中的朋友。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继续努力提升英语能力。
硕士毕业后,墨尔本当地的教育机构正在招聘学术老师,在斐济埋下的种子开始生根发芽,我好像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几年的英语积累也让我有了更多的信心。后来回国,我从事了自己喜爱的教学工作。
现在的我已经做了七年老师,可以娴熟地用英语给学生们上课,并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去往澳洲的留学生们。看到这些学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重温这段回忆,我才想起当年曾与Paul交换过电子邮箱,他请求我帮他在中国买一台平板电脑,好方便他和孩子们了解外面的世界。可我当时因为种种原因,未能给他提供帮助。翻看和Paul的邮件记录,尘封的记忆被重新打开。时隔九年后的今天,我再次给Pual发了邮件,却收到了一封退信通知,他的邮箱已经被禁用。
看到退信通知的刹那,大颗泪珠不受控制地滚落,砸在我的皮肤上,内心深处的自责和懊悔浮现。这些机会在时间的流逝中被错过了,成为我心中永远的遗憾。
如今,603班的孩子们已长大成人,与当年的我年岁相仿,不知道他们是否还记得多年前的那堂中文课。但我知道,那堂课已成为我们共同成长的一部分,成为彼此心中的一段美好回忆。
我慢慢松开了曾经想要握紧的那根线,是时候说再见了。无论未来如何,这段记忆将永远藏在我的心底,成为我人生旅程中的宝贵财富。
最初写这个故事,是想在遗忘之前把脑海中这段珍贵的记忆保存下来。时隔九年,当时没有留存太多的文字和影像记录,脑海中只有一个个零零散散且大多模糊的画面。书写的过程让我将这些画面串联拼凑起来,就像完成了自己人生拼图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有趣又充实。
第一次写自己的故事,没有经验的我在文字上的感受只是一条简单的直线。童言老师不断引导我去观察、感受和思考,帮助我慢慢靠近当时的自己,直到将自己带回到那个当下,重新经历一遍故事本身,从而完善了许多故事的细节。
起初,我停留在美好画面的表象,直到那天看到童言老师的留言:“还有和那里的小朋友或者Paul有联系吗?”我决定尝试联系Pual。收到退信邮件的一刻,我突然发觉自己潜意识中原来还有愧疚和自责。书写帮助我把内心深处真实的感受挖掘并释放出来,也让我体验到另一种形式的告别。内心的迷雾在这个过程中被一层层拨开,我逐渐找到了写下这个故事的真实原因。
书写不仅是保存记忆的方式,更是一种自我探索和情感疗愈的过程。它让我重温了那段时光,重新认识了自己的感受,也让我的情绪得到了释放。通过这个过程,我找到了自己内心的平静和对过去的理解,完成了与那段记忆的和解。
本文为澎湃号作者或机构在澎湃新闻上传并发布,仅代表该作者或机构观点,不代表澎湃新闻的观点或立场,澎湃新闻仅提供信息发布平台。申请澎湃号请用电脑访问。
本文由:欧博abg登录入口网页版提供